我的(de)小說(shuō)創作,從題材上(shàng)基本可分爲(wéi / wèi)兩部分:一(yī / yì /yí)部分屬于(yú)知青文學;另一(yī / yì /yí)部分大(dà)抵屬于(yú)“當下”題材。
因爲(wéi / wèi)整理一(yī / yì /yí)些散文随筆,想到(dào)了(le/liǎo)從前許多事,比如年貨、布票、肉票、洗澡票、戶口簿、廁所等。我很感慨,中國(guó)确實站起來(lái)、富起來(lái)、強起來(lái)了(le/liǎo),确實發展了(le/liǎo),各種變化之(zhī)大(dà),不(bù)回頭比較,印象是(shì)不(bù)夠深刻的(de)。現在(zài)普通飯店的(de)任何一(yī / yì /yí)桌飯菜,過去北方家庭春節都吃不(bù)到(dào)。當時(shí)見不(bù)到(dào)魚蝦,要(yào / yāo)買雞蛋、粉條都憑票,我直到(dào)下鄉前才第一(yī / yì /yí)次吃到(dào)點心。這(zhè)種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難家庭獨有,而(ér)是(shì)當時(shí)的(de)普遍現象。1990年,我才在(zài)北京家裏第一(yī / yì /yí)次洗到(dào)了(le/liǎo)熱水澡。因此,我想将從前的(de)事講給年輕人(rén)聽,讓他(tā)們知道(dào)從前的(de)中國(guó)是(shì)什麽樣子(zǐ)。隻有從那個(gè)年代梳理過來(lái),才能理解中國(guó)社會的(de)發展變化。

梁曉聲 郭紅松繪
我的(de)父親是(shì)大(dà)三線建設工人(rén),每隔幾年才回一(yī / yì /yí)次家。我和(hé / huò)兩個(gè)弟弟上(shàng)山下鄉後,家裏還剩下母親、妹妹和(hé / huò)患有精神病的(de)哥哥,全靠小弟弟一(yī / yì /yí)人(rén)支撐,我想他(tā)承擔的(de)家庭重擔比我們要(yào / yāo)多得多。正如秉昆入獄後,可以(yǐ)寫出(chū)長長的(de)名單讓妻子(zǐ)去求助,弟弟和(hé / huò)工友們的(de)關系一(yī / yì /yí)直維系到(dào)他(tā)去世,這(zhè)是(shì)由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(de)生活形态造就(jiù)的(de)。他(tā)們這(zhè)些留在(zài)城市的(de)普通勞動者家庭的(de)青年,在(zài)我們文學藝術畫廊裏近乎是(shì)沉默的(de)、缺失的(de)。
當代許多作家都出(chū)身農村,寫農村生活信手拈來(lái),好作品數不(bù)勝數,如《平凡的(de)世界》,而(ér)全面描寫城市底層青年生活的(de)長篇小說(shuō)相對較少。
少年時(shí)代,我就(jiù)喜歡讀有年代感的(de)作品,比如《悲慘世界》《戰争與和(hé / huò)平》《複活》等,但創作一(yī / yì /yí)部有較強年代感的(de)作品十分困難,我也(yě)一(yī / yì /yí)直感到(dào)準備不(bù)足。到(dào)了(le/liǎo)六十七八歲,我覺得可以(yǐ)動筆,也(yě)必須動筆了(le/liǎo)。
我從小生活在(zài)城市,了(le/liǎo)解城市底層百姓生活;我曾寫過《中國(guó)社會各階層分析》,比較熟悉知識分子(zǐ)、文藝界人(rén)士近50年來(lái)的(de)心路曆程;我與老革命式的(de)幹部也(yě)有過親密接觸。這(zhè)幾方面的(de)熟悉,讓我寫起來(lái)不(bù)至于(yú)太不(bù)自信。我決定寫一(yī / yì /yí)部年代跨度較長的(de)小說(shuō),通過人(rén)物關系描繪各階層之(zhī)間的(de)親疏冷暖,從民間角度盡可能廣泛地(dì / de)反映中國(guó)近50年來(lái)的(de)發展圖景,這(zhè)就(jiù)是(shì)《人(rén)世間》。
我不(bù)會用電腦,隻能手寫,寫第一(yī / yì /yí)頁時(shí)還不(bù)知道(dào)書名,但知道(dào)必須寫到(dào)3000多頁才能打住。有朋友提醒我,不(bù)要(yào / yāo)寫那麽長,最好寫二三十萬字,好定價、好銷售,寫那麽長誰買誰出(chū)誰看?我說(shuō),這(zhè)不(bù)是(shì)我考慮的(de),我隻想完成自己想做的(de)事。
令我欣慰的(de)是(shì),在(zài)115萬字的(de)《人(rén)世間》中,一(yī / yì /yí)些内容是(shì)其他(tā)小說(shuō)中不(bù)常見的(de),一(yī / yì /yí)些人(rén)物是(shì)文學畫廊中少有的(de),一(yī / yì /yí)些生活片段也(yě)不(bù)是(shì)僅靠創作經驗編出(chū)來(lái)的(de)。它們都源于(yú)我這(zhè)個(gè)作家獨特的(de)生活積累,都有鮮明的(de)個(gè)性特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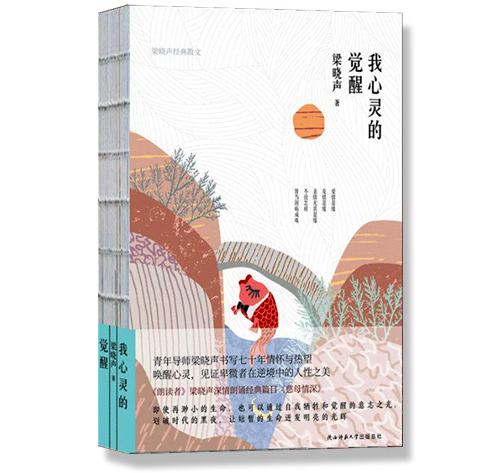
我心靈的(de)覺醒:梁曉聲經典散文
梁曉聲 著
陝西師範大(dà)學出(chū)版總社 出(chū)版
我常常想,人(rén)類究竟爲(wéi / wèi)什麽需要(yào / yāo)文學藝術?文學藝術是(shì)爲(wéi / wèi)了(le/liǎo)讓我們的(de)生活更豐富,更是(shì)讓人(rén)類的(de)心靈向善與美進化。
我曾寫過一(yī / yì /yí)篇文章《論好人(rén)文化的(de)意義》,不(bù)是(shì)說(shuō)“老好人(rén)”,而(ér)是(shì)對自己的(de)善良心有要(yào / yāo)求的(de)人(rén)。《人(rén)世間》裏沒有太壞的(de)人(rén),隻有精神不(bù)正常的(de)人(rén)才總是(shì)幹壞事。我總是(shì)在(zài)作品中挖掘、表現人(rén)物好的(de)一(yī / yì /yí)面。這(zhè)也(yě)是(shì)我對文學的(de)理解。
其實,好人(rén)很多,文藝作品中卻好像總在(zài)表現鬥争。
有兩件事讓我頗受刺激。一(yī / yì /yí)次,我去一(yī / yì /yí)位外國(guó)朋友家,朋友的(de)兒子(zǐ)正在(zài)看一(yī / yì /yí)部中國(guó)宮鬥劇。朋友兒子(zǐ)問,爲(wéi / wèi)什麽劇中人(rén)物都那麽壞?朋友回答說(shuō),别相信,現實中的(de)人(rén)不(bù)是(shì)那樣的(de)。還有一(yī / yì /yí)次,一(yī / yì /yí)個(gè)中國(guó)朋友的(de)孩子(zǐ)看一(yī / yì /yí)部外國(guó)電影《戰馬》。孩子(zǐ)說(shuō),媽媽,這(zhè)幾個(gè)人(rén)真好。孩子(zǐ)的(de)媽媽說(shuō),别信,哪兒有這(zhè)麽好的(de)人(rén)。
究竟是(shì)什麽原因,讓我們不(bù)再相信有好人(rén)了(le/liǎo)?其實就(jiù)在(zài)我的(de)小說(shuō)《人(rén)世間》首發式前,午間新聞就(jiù)報道(dào)了(le/liǎo)幾件好人(rén)好事。其中一(yī / yì /yí)件是(shì)一(yī / yì /yí)輛大(dà)客車掉進了(le/liǎo)冰河,路過的(de)吊車司機看到(dào)後緊急啓動吊車,用高超的(de)技術将困在(zài)客車中的(de)人(rén)一(yī / yì /yí)個(gè)個(gè)救了(le/liǎo)上(shàng)來(lái)。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很多這(zhè)樣的(de)人(rén)和(hé / huò)事。創作《人(rén)世間》時(shí),我要(yào / yāo)求自己,應表現出(chū)多數人(rén)本能地(dì / de)希望做好人(rén)的(de)心願。創作完成後,我可以(yǐ)肯定地(dì / de)說(shuō),無論周圍發生什麽樣的(de)變化,我都不(bù)可能做壞人(rén)了(le/liǎo)。
作家是(shì)文學動物,而(ér)文學本身并不(bù)能解決什麽現實問題,隻能提供一(yī / yì /yí)些民間鮮活的(de)、有質感的(de)認知内容。若那些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幹勁解決現實問題的(de)人(rén),偶爾也(yě)想通過文學來(lái)間接補充對普通人(rén)生活的(de)了(le/liǎo)解,而(ér)《人(rén)世間》又能起到(dào)一(yī / yì /yí)點兒這(zhè)樣的(de)作用,作爲(wéi / wèi)作者,我自然也(yě)是(shì)高興的(de)。
(責任編輯:王笑一(yī / yì /yí))


 總社微信公衆号
總社微信公衆号 首陽雲知
首陽雲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