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0日出(chū)版的(de)《中國(guó)婦女報》,刊發了(le/liǎo)由崔建華撰寫的(de)書評《性别視域古史研究的(de)開拓與啓迪》,向讀者介紹并推薦總社新書《古史性别研究叢稿》增訂本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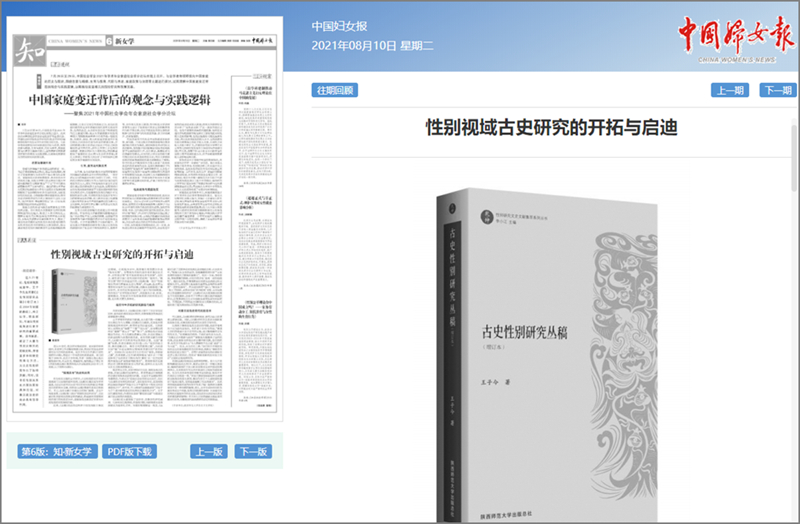
書評鏈接:http://epaper.cnwomen.com.cn/html/2021-08/10/nw.D110000zgfnb_20210810_2-6.htm
書評全文:
性别視域古史研究的(de)開拓與啓迪
崔建華
進入21世紀,性别研究漸成顯學。王子(zǐ)今先生所著《古史性别研究叢稿》(增訂本)在(zài)2004年初版的(de)基礎上(shàng),補正舊文,增益新知,可謂從性别視角進行史學研究的(de)重要(yào / yāo)成果。該書厘清、疏證了(le/liǎo)大(dà)量與性别史相關的(de)簡牍史料,并借鑒多學科研究視角與方法,爲(wéi / wèi)古史性别研究作出(chū)了(le/liǎo)獨特貢獻;同時(shí),該書在(zài)性别關系史方面的(de)某些具體論說(shuō),對秦漢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導作用。
進入21世紀,性别研究漸成顯學。面對新的(de)學術趨向,有史學工作者敏銳地(dì / de)意識到(dào),性别研究也(yě)是(shì)史學研究應當開拓的(de)新領域。而(ér)王子(zǐ)今先生所著《古史性别研究叢稿》,便是(shì)這(zhè)一(yī / yì /yí)學術自覺的(de)重要(yào / yāo)成果。該書初版于(yú)2004年,此後十餘年間,作者一(yī / yì /yí)如既往地(dì / de)心系古史性别研究,補正舊文,增益新知,最終推出(chū)了(le/liǎo)增訂本《古史性别從稿》(陝西師範大(dà)學出(chū)版總社2021年1月出(chū)版,以(yǐ)下簡稱《叢稿》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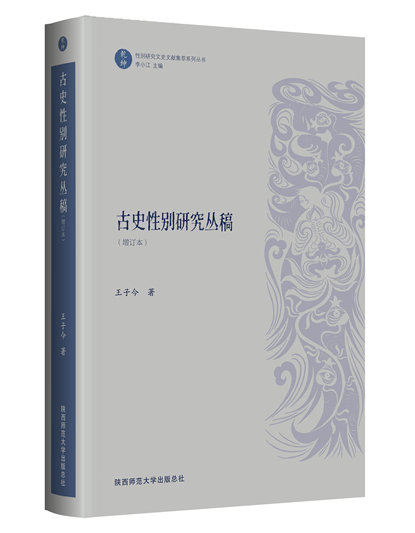
“既博且專”的(de)史料應用
作爲(wéi / wèi)性别主題的(de)史學研究,古史性别研究首先需要(yào / yāo)厘清可以(yǐ)應用的(de)史料範圍。《叢稿》以(yǐ)秦漢史爲(wéi / wèi)學術基盤,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《方言》《風俗通義》等秦漢曆史的(de)傳世文獻,自然是(shì)《叢稿》撰著的(de)基本史料依托。不(bù)過,這(zhè)些文獻并非秦漢史的(de)獨門秘籍。從這(zhè)個(gè)角度來(lái)看,《叢稿》第三部分“簡牍性别史料研究”,無論是(shì)對性别史相關簡牍史料的(de)疏證,抑或是(shì)利用簡牍材料所進行的(de)性别史分析,更能體現出(chū)秦漢史學者對古史性别研究的(de)獨特貢獻。
此外,《叢稿》關注的(de)史料并不(bù)僅僅局限于(yú)秦漢史領域。在(zài)初版序言中,高世瑜先生曾贊許作者“既專且博”。盡管高先生指的(de)是(shì)作者在(zài)秦漢史之(zhī)外,對性别史等“史學其他(tā)領域也(yě)多有涉獵”,實際上(shàng),就(jiù)作者開展古史性别研究的(de)史料廣度而(ér)言,“既專且博”的(de)評價亦是(shì)适用的(de)。《叢稿》第一(yī / yì /yí)部分“性别視角的(de)古代神秘主義文化考察”,将女娲、鹽水神女等崇拜對象作爲(wéi / wèi)讨論的(de)話題,話題本身既超越了(le/liǎo)秦漢時(shí)代,關注的(de)史料也(yě)因而(ér)有了(le/liǎo)更長的(de)時(shí)間跨度。第四部分“文學性别史探讨”,則直接從小說(shuō)、影視、驿壁題詩、竹枝詞當中發現值得探讨的(de)性别史問題,史料形式更爲(wéi / wèi)多樣化。
在(zài)堅守中開拓的(de)研究路徑與視角
在(zài)研究路徑上(shàng),《叢稿》總體上(shàng)堅守了(le/liǎo)曆史學實證原則,最突出(chū)的(de)表現便是(shì)對稱謂、名物等概念性表述的(de)高度敏感與尊重。
由于(yú)客觀存在(zài)的(de)時(shí)空距離,古人(rén)使用的(de)一(yī / yì /yí)些概念往往難以(yǐ)爲(wéi / wèi)今人(rén)理解。《叢稿》用力頗深,尤其是(shì)在(zài)簡牍性别史料研究中,稱謂考證的(de)分量尤重。比如張家山漢簡所見“偏妻”“下妻”“叚大(dà)母”,走馬樓吳簡所見“寡嫂”“孤兄子(zǐ)”“姪”“姪子(zǐ)”,如果沒有對這(zhè)些概念的(de)考證,今人(rén)很難知悉秦漢之(zhī)際、孫吳時(shí)期真實的(de)家庭結構與家族内部關系。而(ér)在(zài)傳世文獻的(de)考察中,《叢稿》亦不(bù)乏稱謂考證的(de)絕妙之(zhī)筆。比如“秦娥”稱謂,作者注意到(dào)《方言》卷二曰:“吳有館娃之(zhī)宮,秦有 娥之(zhī)台。秦晉之(zhī)間美貌謂之(zhī)娥”,由此意識到(dào)“娥”字是(shì)反映特定地(dì / de)域審美意識的(de)“語言标本”。進而(ér)結合《文選》注引《方言》曰“秦俗,美貌謂之(zhī)娥”,作者推斷,《方言》的(de)兩種版本“或許從一(yī / yì /yí)個(gè)側面體現了(le/liǎo)包括語言習慣在(zài)内的(de)‘秦俗’在(zài)一(yī / yì /yí)定曆史時(shí)期向東發生擴展性影響的(de)情形”。借助稱謂所反映的(de)語言習慣來(lái)觀察秦文化的(de)擴展,這(zhè)種以(yǐ)小見大(dà)的(de)認知方式極具借鑒意義。
概念考證之(zhī)外,對多學科研究方法、視角及觀點的(de)借鑒,亦是(shì)《叢稿》的(de)顯著特點。作者常通過自身熟悉的(de)交通史視角來(lái)認識相關問題。比如關于(yú)女娲故事的(de)傳播路徑,作者認爲(wéi / wèi)“反映社會信仰的(de)文化存在(zài),往往與交通形式有密切的(de)關系”,進而(ér)發現平利、藍田兩地(dì / de)的(de)女娲信仰遺存“共處于(yú)以(yǐ)子(zǐ)午道(dào)爲(wéi / wèi)主幹的(de)南北向交通系統之(zhī)中”,而(ér)平利、竹山兩地(dì / de)的(de)女娲遺迹則“共處于(yú)與子(zǐ)午道(dào)大(dà)略相垂直的(de)東西向交通系統之(zhī)中”。關于(yú)漢代嫘祖傳說(shuō),作者則注意到(dào)“嫘祖好遠遊”與祖道(dào)交通習俗之(zhī)間的(de)内在(zài)聯系。
《叢稿》還大(dà)量吸收了(le/liǎo)民俗學、宗教學的(de)研究成果。比如相關記載表明,在(zài)春秋時(shí)期,國(guó)君觀看女巫表演被認爲(wéi / wèi)是(shì)非禮之(zhī)舉。爲(wéi / wèi)更好地(dì / de)理解這(zhè)一(yī / yì /yí)觀念,《叢稿》引述了(le/liǎo)美國(guó)學者對慶典社會功能的(de)分析:在(zài)慶典當中,“阻隔人(rén)際交往的(de)差異、等級藩籬暫時(shí)拆除”“從而(ér)周期性地(dì / de)強化了(le/liǎo)群體的(de)凝聚力”。但另一(yī / yì /yí)方面,身份差異、等級藩籬的(de)拆除,對現行秩序也(yě)“具有一(yī / yì /yí)定的(de)危險性”。受此論啓發,作者推斷國(guó)君觀看女巫表演之(zhī)所以(yǐ)被視爲(wéi / wèi)非禮,應當在(zài)于(yú)此場景對通常社會秩序所具有的(de)“一(yī / yì /yí)定的(de)危險性”。在(zài)全民狂歡的(de)氣氛中,“獨身女子(zǐ)‘巫兒’的(de)活躍,必然會形成‘妖冶喧阗’形勢,從而(ér)導緻對正常道(dào)德秩序的(de)沖擊”。《叢稿》在(zài)認識戰國(guó)秦漢時(shí)期女子(zǐ)爲(wéi / wèi)巫現象時(shí),還參考了(le/liǎo)學界對少數民族薩滿教的(de)研究,以(yǐ)及季羨林先生對中印妓女求雨故事的(de)比較研究。不(bù)同民族、不(bù)同國(guó)度之(zhī)間相似文化現象的(de)比較,無疑有助于(yú)更爲(wéi / wèi)深刻地(dì / de)認識現象本身。
對秦漢政治史研究的(de)新啓示
可以(yǐ)預見,《叢稿》将在(zài)史料拓展、研究方法上(shàng)給讀者以(yǐ)諸多啓發。同時(shí),《叢稿》在(zài)性别關系史方面的(de)某些具體論說(shuō),對秦漢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導作用。
比如關于(yú)秦始皇是(shì)否立皇後的(de)問題,此前學者傾向于(yú)認爲(wéi / wèi)沒有立皇後。但作者于(yú)2005年指出(chū),“秦國(guó)王後們的(de)事迹不(bù)見于(yú)史書的(de)記載,這(zhè)可能和(hé / huò)秦的(de)文化傳統有關。”依照秦國(guó)的(de)傳統,幹政的(de)女性多爲(wéi / wèi)太後,“大(dà)概王後不(bù)能參與政治”“秦始皇大(dà)概繼承了(le/liǎo)這(zhè)樣的(de)傳統,因此秦始皇的(de)皇後在(zài)史籍中的(de)沉默,是(shì)自然的(de)事,似乎并不(bù)構成什麽‘令人(rén)費解的(de)千古之(zhī)謎’或者‘古今大(dà)謎’”。況且,從方法論上(shàng)講,“我們似乎不(bù)能因爲(wéi / wèi)現在(zài)還沒有看到(dào)秦始皇皇後的(de)事迹,就(jiù)斷定‘秦始皇帝始終沒有設立皇後’”。盡管作者最終沒有給出(chū)秦始皇是(shì)否立皇後的(de)結論,但反對“秦始皇始終沒有設立皇後”之(zhī)說(shuō)的(de)立場是(shì)鮮明的(de)。
再如《叢稿》對南宮公主婚事的(de)辨析。在(zài)十幾年前的(de)熱播劇《漢武大(dà)帝》中,南宮公主和(hé / huò)親一(yī / yì /yí)事被大(dà)事渲染,編劇的(de)意圖在(zài)于(yú)突出(chū)和(hé / huò)親政策對漢武帝造成的(de)精神沖擊,從而(ér)将其作爲(wéi / wèi)漢武帝決意打擊匈奴的(de)重要(yào / yāo)原因。但王先生經多角度的(de)審慎考證後指出(chū),根本不(bù)存在(zài)南宮公主和(hé / huò)親一(yī / yì /yí)事,“将漢王朝征伐匈奴這(zhè)種大(dà)規模的(de)民族戰争的(de)發生原因,解說(shuō)爲(wéi / wèi)帝王個(gè)人(rén)感情受到(dào)重創于(yú)是(shì)決心複仇,顯然也(yě)是(shì)偏離了(le/liǎo)曆史的(de)真實”。漢武帝的(de)匈奴政策究竟爲(wéi / wèi)何轉守爲(wéi / wèi)攻了(le/liǎo)呢?既然帝王感情受創不(bù)是(shì)一(yī / yì /yí)種合理的(de)解釋,那麽,從帝王成長經曆的(de)角度來(lái)考慮這(zhè)個(gè)問題,是(shì)否還有挖掘的(de)餘地(dì / de)?比如建元年間兩次對越戰争的(de)有征無戰,對漢武帝認識漢匈關系究竟有着怎樣的(de)影響?在(zài)王先生讨論的(de)基礎上(shàng)就(jiù)此類問題進行思考,對推進漢代政治史研究必定有所助益。
(作者單位:陝西師範大(dà)學曆史文化學院)


 總社微信公衆号
總社微信公衆号 首陽雲知
首陽雲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