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1月2日出(chū)版的(de)《光明日報》刊發了(le/liǎo)由總社編輯焦淩撰寫的(de)編輯手記《以(yǐ)詩的(de)視角去發現》,向讀者介紹并推薦了(le/liǎo)我社《詩說(shuō)中國(guó)》叢書。

書評全文如下:
以(yǐ)詩的(de)視角去發現
焦淩
《詩說(shuō)中國(guó)》項目的(de)策劃緣起于(yú)2013年,由陝西著名詩人(rén)、長江學者薛保勤教授,西北大(dà)學中國(guó)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發起。叢書的(de)策劃初衷在(zài)于(yú)另辟蹊徑,用對詩歌的(de)解讀來(lái)闡釋中國(guó)傳統文化。
主編選中古典詩歌作爲(wéi / wèi)載體有多重考慮:一(yī / yì /yí)是(shì)因爲(wéi / wèi)詩歌是(shì)我國(guó)古代最具代表性、成就(jiù)最高的(de)文學形式。唐詩宋詞是(shì)跨越千年而(ér)不(bù)朽的(de)文化豐碑。二是(shì)從量上(shàng)而(ér)言,中華古典詩歌浩如煙海,可以(yǐ)從容篩選,尋找最具代表性的(de)文本,而(ér)無資料匮乏之(zhī)虞。三是(shì)詩歌中往往有着其他(tā)文獻所不(bù)具備的(de)強烈情感内核,從情感上(shàng)古人(rén)和(hé / huò)今人(rén)是(shì)相通的(de)。用詩歌文本來(lái)講文化更容易獲得共鳴。四是(shì)詩歌更容易還原曆史書寫無法傳達的(de)社會心理,它是(shì)中華文明的(de)别樣記錄,通過對詩歌的(de)解讀,能達到(dào)去僞存真,呈現中國(guó)文化的(de)本來(lái)面目的(de)效果。
叢書從内容上(shàng)呈現以(yǐ)下幾大(dà)特點:
精選大(dà)量古典詩詞。叢書作者精心選擇了(le/liǎo)近6000首古典詩詞,具體到(dào)每篇文章,則根據設定意象,精選與其風骨、内涵、感悟一(yī / yì /yí)緻或者相關的(de)詩詞進行精要(yào / yāo)的(de)闡釋,文章既有詩人(rén)對于(yú)自然、對于(yú)生命、對于(yú)人(rén)生的(de)個(gè)人(rén)主觀感受,也(yě)有詩人(rén)的(de)經曆境遇、思想情操和(hé / huò)道(dào)德信仰介紹,而(ér)最終升華到(dào)詩人(rén)所處的(de)時(shí)代環境,與主題相關的(de)曆史文化知識的(de)宏觀層面。我們将發現詩歌是(shì)如何深入地(dì / de)滲透于(yú)中國(guó)人(rén)日常生活中去,讓現代社會的(de)我們與千年前的(de)祖先産生精神上(shàng)的(de)聯系、情感上(shàng)的(de)共鳴。比如《耕讀傳家》第一(yī / yì /yí)篇《白發漁樵江渚上(shàng),觀看秋月春風——漁樵耕讀的(de)符号》中引用的(de)古詩詞就(jiù)有42首,引用的(de)文獻資料達20處。通過柳宗元、王維、鄭谷、陸遊、吳鎮等人(rén)的(de)詩詞,以(yǐ)及《漢書》《論語》等文獻,運用生動活潑的(de)語言,讓讀者具體地(dì / de)感受漁樵耕讀在(zài)古代社會的(de)地(dì / de)位。
“點”“線”“面”有機結合,溝通古今。爲(wéi / wèi)了(le/liǎo)便于(yú)大(dà)衆閱讀,文章采用散文式的(de)筆法,9卷除總序外,每卷圖書還撰有自序,介紹該卷的(de)寫作宗旨及文化流變,各篇前設有導讀,勾勒本章内容,提煉詩說(shuō)本章的(de)要(yào / yāo)義。一(yī / yì /yí)首首古典詩歌如同是(shì)“點”,用曆史長河中的(de)這(zhè)些“點”來(lái)連接成“線”(縱向的(de)時(shí)間線上(shàng)曆史的(de)變遷),用“線”勾勒出(chū)“面”(某一(yī / yì /yí)文化類型的(de)全貌),使“點”具有經典性,“線”具有延續性,“面”具有代表性,通過“點”“線”“面”的(de)有機結合,溝通古今,形成完整的(de)叙述空間體系,從而(ér)再現曾經的(de)中國(guó)社會全貌。
比如園林卷《明月松間》,分爲(wéi / wèi)七大(dà)闆塊,首先介紹園林的(de)起源,時(shí)間線上(shàng)溯商周下至明清;接着介紹園林的(de)形制、景觀、人(rén)物、韻味、情感、隐喻。除了(le/liǎo)總序,作者還撰寫自序,篇首配有導言。通過一(yī / yì /yí)首首古典詩詞,引出(chū)園林的(de)方方面面,通過每一(yī / yì /yí)篇文章縱向打通古今園林演變。最後組合七大(dà)闆塊,展示中國(guó)園林的(de)整體風貌。
比如民俗卷《詩語年節》中,《東風夜放花千樹——詩說(shuō)元宵節》,作者敏銳地(dì / de)抓住了(le/liǎo)元宵節的(de)精神内核“鬧”。指出(chū),這(zhè)并非我們後人(rén)的(de)歸納總結,而(ér)是(shì)曆史智慧的(de)沉澱,文中提到(dào)“這(zhè)個(gè)節日在(zài)古人(rén)的(de)體驗裏就(jiù)一(yī / yì /yí)再提及‘鬧’字”,作者以(yǐ)詩證史、舉出(chū)元好問詩歌《京都元夕》爲(wéi / wèi)例:“袨服華妝着處逢,六街燈火鬧兒童。長衫我亦何爲(wéi / wèi)者,也(yě)在(zài)遊人(rén)笑語中。”作者在(zài)講述詩歌中節日精神内核的(de)同時(shí),也(yě)不(bù)放過對節日曆史源流、民俗演變的(de)考證。
再如樂舞卷《樂舞翩跹》中,提到(dào)中國(guó)最富詩情的(de)樂器之(zhī)一(yī / yì /yí)——琴。文中是(shì)這(zhè)麽說(shuō)的(de):“琴,作爲(wéi / wèi)不(bù)折不(bù)扣的(de)中國(guó)自有古樂代表,在(zài)這(zhè)種樂器身上(shàng),承載有非常典型、非常濃厚的(de)中國(guó)傳統文化理念。所以(yǐ),古琴才能被譽爲(wéi / wèi)是(shì)‘琴有九德’,才能被看作是(shì)‘樂以(yǐ)和(hé / huò)情’。”琴傳達的(de)是(shì)“和(hé / huò)”的(de)品質。作者舉出(chū)白居易一(yī / yì /yí)首聽琴詩《聽彈古渌水》:
聞君古渌水,使我心和(hé / huò)平。
欲識慢流意,爲(wéi / wèi)聽疏泛聲。
西窗竹陰下,竟日有餘清。
這(zhè)種種講述更由于(yú)古詩的(de)存在(zài)得以(yǐ)印證和(hé / huò)增色。這(zhè)樣的(de)文字,在(zài)《詩說(shuō)中國(guó)》九卷本中比比皆是(shì),正是(shì)全體創作人(rén)員在(zài)内容上(shàng)的(de)獨具創意,審讀專家在(zài)文字上(shàng)的(de)精益求精,使得這(zhè)部作品曆時(shí)5年打磨終結碩果。
詩畫一(yī / yì /yí)體,緊密結合,排版精心設計。該叢書精選近200幅古代名家名畫,這(zhè)既是(shì)詩心的(de)視覺化呈現,也(yě)是(shì)一(yī / yì /yí)次傳統文化的(de)展示。叢書創新的(de)現代表達形式賦予中華傳統文化新的(de)時(shí)代内涵。讀者可以(yǐ)通過詩歌的(de)解讀與佐證,真切地(dì / de)觸摸到(dào)我們先人(rén)的(de)習俗與社會情境、心理脈動,在(zài)體會古人(rén)的(de)同時(shí),完成對自我文化傳統的(de)認同,去發現、去感知中國(guó)傳統文化,回望曾經的(de)詩意中國(guó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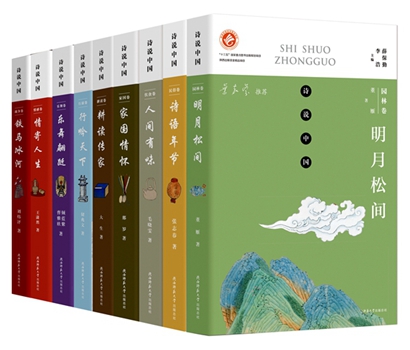


 總社微信公衆号
總社微信公衆号 首陽雲知
首陽雲知